推荐阅读
l 梦的工作部分
1. 《荣格全集》第16卷中“梦的分析的实践应用”一章,作者卡尔·荣格。(见附录)
2. 《荣格心理学手册》第11章“梦”(本章作者玛丽·安·马顿),本书作者雷诺斯·帕帕多普洛斯
l 积极想象部分
1. 《红书》,作者荣格
2. 《红书》导读部分,卡尔·荣格原著/索努·沙姆达萨尼(Sonu Shamdasani)编译
3. 《荣格心理学手册》第10章“积极想象”(本章作者琼·乔多罗),本书作者雷诺斯·帕帕多普洛斯
附录(本材料引自未出版书籍,仅可内部学习使用,不可外传,违者追求法律责任)
Ⅱ 梦的分析的实践运用
【原文是1931年在德累斯顿的国际全科医学心理治疗协会第六届大会上发言。
发表为 "Die praktische Verwendbarkeit der Traumanalyse" in Wirklichkeit der Seele (Zurich, 1934), pp. 68-103.】
李孟潮译
294心理治疗中梦分析的应用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许多从业者发现在神经症治疗中梦分析是不可或缺的,并且认为梦是一种功能,其精神重要性和意识心灵本身相等。其他人则相反,质疑梦分析的价值,并认为梦是一种精神的可忽略副产品。显然,如果一个人持有的观点是——“无意识在神经症病因学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话,那么他就会赋予作为无意识直接表达的梦很高的实践重要性。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他否认了无意识,或者至少认为无意识在病因学方面无意义,他就会低估梦分析的重要性。无意识的实际存在性还仍会成为有争论之事,这也许应当被看做是一种遗憾,在西元1931这一年,在卡鲁斯(Carus)阐述无意识的概念多过半个世纪后,在康德提出“模糊理念的无限领域”(illimitable field of obscure ideas)多过一个世纪后,在莱布尼茨假设无意识精神活动将近200年后,更不用提让内(Janet)、弗卢努瓦(Flournoy)(译者注:Théodore Flournoy,1854 –1920,瑞士日内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主要研究通灵等现象, 其工作影响到了荣格对其表妹,也是通灵者Héléne Preiswerk的研究)、弗洛伊德,以及在所有这些人之后的很多人。但是,既然我的意图是专门来处理实践问题,所以我不会在此深入,用无意识问题来替代此主题,虽然我们的梦分析的特定问题与此假说休戚相关。没有这个假说,梦仅仅是自然的怪物,白日留下的碎片的无意义聚集物而已。要是梦真是如此的话,那现在这个讨论就没有理由成立了。除非我们承认无意识,否则我们根本就无法处理这个主题,因为梦分析宣称的目标不仅是来锻炼我们的机智,而是解释和认识那些迄今仍是无意识的内容,它们被认为对于阐明或治疗神经症是有重要意义的。任何人发现这个假说是无法接受的,那么他必然会简单地排除梦分析运用这个问题。
295但是既然根据我们的假设,无意识过程具有病因学意义,而且既然梦是无意识精神活动的直接表达,那么尝试分析和解释梦,从科学立场上来看,就是理论上正当的。如果成功,我们就可以期待——除了可能获得某些治疗效果以外——这种尝试可以给与我们关于精神因果性结构的科学洞见。然而,从业者倾向于认为,科学发现——至多——只是其治疗工作令人满意的副产品,所以,他几乎不会把梦分析实践运用的充足理由,当做是对其病因学背景的理论领悟这一极小可能性之事,更不用说把此事当做适应症了。当然,他也许会相信,如此获得的解释性领悟是有治疗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把梦分析提升为一种职业责任。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的坚定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治疗结果,恰恰是通过阐明无意识的因果因素获得的——也就是说,把这些因素解释给病人,并让病人充分意识到其困难的来源。
296假定此刻这种期望已经因事实而被证明有理,那么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是否梦分析能被单独使用或是与其他方法联合使用,用来发现无意识的病因。弗洛伊德派对此问题的答案——我假设是——“常识”。我能证实这个答案,因为梦,尤其是是治疗开始时期出现的初始梦,往往以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启明基本的病因学因素。下面这个例子可供说明:
297有一位男子在世间地位显赫,来找我谘询。他被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而折磨,并抱怨有不时出现的眩晕感,导致了恶心、头重和呼吸窘迫感——这个状态很容易和高山病混淆。(译者注:高山病,是指到3000米以上高山,由于缺氧,肺动脉痉挛引起肺高压的一系列症状。)他已经有非同寻常、无比成功的事业,而且凭藉着抱负、勤奋和天赋,从其作为贫穷农夫儿子的卑微出身步步高升。他一步步往上爬,最终达到了领导之位,拥有进一步社会晋升的一切前景。他现在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他可以一飞冲天的跳板,要不是其神经症突然介入的话。在其故事讲到此处之时,病人禁不住发出了他那常见的感叹,这种感叹总是以这样的套话开头:“正在此时,当……”。他具有高山病的所有症状这一事实,看起来作为其特殊困境的鲜明图解是非常合适的。他也把前一晚的两个梦带到了谘询中。第一个梦如下:我又回到了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一些以前和我一起去上学的农村伙伴们都站在街道中。我走过去,装作不认识他们。然后我听到他们中一人,指着我说:“他不常回到我们村来。”
298要看到在这个梦中所指示的梦者职业的卑微起源,并理解这个指示的意义为何,并不要求任何解释的技艺。梦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你忘记了你开始的时候是多么底层。”
299这里是第二个梦:“我非常忙碌,因为我要继续一段旅程。我不停地在找要打包的东西,但是什么都找不到。时间飞逝,火车很快就要开走了。终于最后我成功地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了,我沿着街道匆忙赶路,结果却发现我遗忘了一个装有重要档的公事包。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回去,终于发现了公事包,然后又冲往车站,但是我几乎不能前进。我竭尽全力,冲到了月台上,结果却看到火车刚好冒着烟离开月台。火车非常的长,以奇怪的S形蜿蜒前进,我突然想到,要是火车司机不小心的话,当他进入直道时加蒸汽的话,后面的车厢还仍然在弯道上,就会因为速度增加而被拋出铁轨。而这就正在发生:火车司机正在加蒸汽,我试图大声呼叫,后面的车厢突然发生可怕的倾斜,被甩出了轨道。那是个可怕的灾难。我在恐惧中醒来。”
300再一次,要理解这个梦的讯息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它描述了病人仍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狂热匆忙。但是因为前面的火车司机持续不断地向前加蒸汽,后面就发生了神经症:车厢摇晃,火车脱轨。
301显然的是,在其生命的目前阶段,病人已经达到了其事业顶点。从其低层出身一路漫长奋力攀登,已耗尽了他的力量。他本应对其成就心满意足,但是与此相反,其野心驱使他一再向前,不断向上,直到进入一种对他来说太过稀薄的气氛中,而对此气氛他是不习惯的。于是他的神经症突袭了他,作为一种警告。
302环境限制我不能进一步治疗这个病人,我关于其情况的观点也不能让他满意。结局是梦中描述的命运自行其道。一个职业空缺诱发了他的野心,他企图趁机而入,而如此猛烈地出轨,以至于灾难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了。
303因此,从意识的既往史中所能推断出来的也就是,高山病是病人无能进一步攀升的象征呈现,这被梦作为事实而证实。
304在此我们遇到了对梦分析运用性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梦描述了梦者的内在状况,而意识心灵否认了其真实性和现实性,或者仅仅是勉强承认。从意识上梦者看不出丝毫理由为什么他不应该稳步前进;相反,他继续其攀登的野心,拒绝承认他自身的无能,而这一点被随后的事件全然证明。只要我们进入意识的领域,我们在面对此类情况总会不太确定。既往史可以以多种方式得到解释。毕竟,列兵在其背包中背着元帅的权杖,很多贫穷父母的儿子获得了最高成功。为什么这里不会是同样的情况?既然我的判断会出错,为什么我的推测就比他自己的更好?在这一点上,梦来到,作为一个超越意识心灵控制的非自主、无意识精神过程。它展现了病人的内在真实和现实,如其真正所是,而不是如我所推测的那样,也不是如他想要的那样,只是如其所是。因此我定下一条规则,正如我对待生理学事实那样对待梦:如果尿中出现了糖,那么尿中就含有糖,不是蛋白质、尿胆素、或其他任何可能更符合我预期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把梦当做是具有诊断学价值的事实。
305正如所有的梦那样,我这个小小的梦的例子给予我们的远超过我们预期的。它不仅给了我们神经症的病因,也给了预后。而且,我们甚至确切地知道了治疗应该从何处开始,我们必须阻止病人全速向前。这正是他在梦中告诉自己的。
306让我们暂且满足于这个提示,回到我们的考虑——梦是否能让我们阐明神经症的病因。我引用的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同样也能引用很多没有任何病因学痕迹的初始梦,尽管它们的含义也是完全清楚的。目前我不希望考虑那些需要锐利分析和解释的梦。
307重点在于:有些神经症其真正病因只有在分析的结束时才变得清楚,还有些神经症其病因是相对不重要的。这带我回到了我们开始时的假说,即为了治疗的目的,绝对有必要让病人对其致病因素有意识化。这个假说和旧有的创伤理论的延伸几无差别。我当然并不否认很多神经症起源于创伤,我只是反对这种提法:所有的神经症的本质都是起源于创伤,都来自童年的某些至关重要体验,毫无例外。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因果性方法 (causalistic approach)。医生必须对病人的过去给予全神关注。他必须总是询问:“为什么?”,而忽视同样中肯的问题,“为了什么?”前者往往对病人有很大的损害效应,病人也许要成年累月,不得不在其记忆中不断搜寻其童年时候某个假设事件,而具有当下重要性之事却被完全地忽略。纯粹的因果性方法太过狭隘,不能充分利用梦以及神经症的真正意义。因此,如果使用梦的目的仅仅是发现病因学因素,这是有偏倚的方法,并且忽视了梦的要点。我们的例子确实显示了足够清晰的病因,并且也提供了预后或对未来的预期,以及有关治疗的建议。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初始梦根本没有触及病因,而是处理非常不同的其他事情,比如病人对医生的态度。作为这一类的例子我想要告诉你们三个梦,全部都是来自同一个病人的,而且每个梦都是在三个不同的分析师那里,在治疗过程的开始做的。这里是第一个梦:“我必须跨越边界进入另一个国家,但是不能找到边界,而且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它在哪里。”
308随后的治疗结果是不成功的,在很短时间后就中断。第二个梦如下:“我必须穿过边界,但是夜晚漆黑一片,我无法找到海关大楼。长期寻找后,我看到在远处有一道微弱光线,我以为边界就在那边。但是要去那边,我必须穿过一个山谷和一个黑森林,在其中我迷路了。这时我注意到有个人在我附近。突然他像个疯子一样紧抓住我,我在恐惧中醒过来。”
309这次治疗,同样,也在几周后中断,因为分析师无意识地把自己认同为病人,而结果是双方都完全丧失了方向。
310第三个梦发生在我的治疗中,“我必须穿越过一个边界,更确切地说,我已经越过了它,并发现我自己在瑞士海关大楼。我只带着一只手提袋,认为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申报。但是海关官员在我的包里翻找,让我吃惊的是,他拖出了一套成对的单人床。”英文:I have to cross a frontier , or rather , I have already crossed it and find myself in a Swiss customs-house. I have only a handbag with me and think 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But the customs official dives into my bag and, to my astonishment , pulls out a pair of twin beds. 德文: Ich muß eine Grenze überschreiten, das heißt ich habe sie schon überschritten und befinde mich in einem schweizerischen Zollhaus. Ich habe nur eine Handtasche und glaube,nichts verzollen zu müssen . Der Zollwächter aber greift in meine Tasche und zieht zu meinem Erstaunen zweiganze Matratzen heraus .”
311在我给她治疗期间,病人结婚了,开始的时候,她产生了对其婚姻极为强烈的阻抗。这种神经症性阻抗的病因在多月之后才大白于天下,而在其梦中对此只字未提。她的梦毫无例外,都是对她和相关医生会遇到的困难的预见。
312这些例子,就像很多此类例子一样,可充分表明,梦经常是预见性的,如完全以纯粹的因果观点来看待它们,就会丧失其特殊意义。它们提供了有关分析情境的正确无误的资讯,对其有正确理解是具有最大的治疗重要性的。A医生正确地理解了这个情境,并把病人移交给B医生。 在B医生的治疗下,病人从梦中自己得出了结论并决定离开。我对于第三个梦的解释让她失望,但是梦显示边界已经被穿越,这一事实鼓励她继续向前,尽管困难重重。
313初始梦往往令人惊叹地清晰明确。但是随着分析工作进展,梦倾向于失去其清楚性。如果发生例外它们仍然保持清楚,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分析还没有触碰到人格的某个重要层面。通常,在治疗开始后不久,梦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晦涩,这也使得解释变得日益困难。进一步的困难是,不久治疗就会达到一个点,说实话,在这个点上医生不再理解作为整体的情境。而他无法理解这一点被梦变得日益费解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因为我们都知道梦的“费解性”完全是医生主观意见。对于理解者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费解的。只有当我们不理解时,事情才会显得不可理解、一片混乱。梦本身是在本质上是清楚的,它们就是它们在特定环境中必须成为的样子。如果我们从治疗的较后阶段,或几年后离远一些来看这些不可理解之梦的话,我们经常会为自己的盲目而大吃一惊。所以如果随着分析进展,我们遭遇到一些——和明晰的初始梦比较起来——显然十分费解之梦,医生不应过于轻易地怪罪梦的混乱,或病人故意阻抗,他要是把这些发现当做是其理解力日渐无力之征兆,就会更好些,就像称呼其病人为“混乱”的精神科医生,应该要认识到这是一个投射,更应说是自己“混乱”一样,因为在现实中是病人的特殊行为让医生的心智被搅乱。而且,医生及时承认他缺乏理解,这在治疗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病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总是被理解更难忍受的了。他通过向医生的职业性自大求助,变得凡事非常依赖医生的神奇力量,并为他设下了危险的陷阱。通过避难于医生的自信和“深刻”理解,病人丧失了所有现实感,陷入顽固的移情中,延迟了治愈。
314 理解明显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它可能是极端片面的,此时医生理解了,而病人不理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医生会设想,他的责任就是要说服病人,而如果后者不愿意自己被说服,医生就会谴责他的阻抗。当理解全部都是在我这边时,我非常镇定地说,我不理解,因为最终医生是否理解无关紧要,而至关重要的是,是否病人理解。因而理解是应该在一致感下出现的理解,而一致感是共同反思的果实。单方面理解的危险性是,医生也许会从先入为主的观念的立场来判断梦。他的判断也许会和正统理论一致,甚至可能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不会赢得病人的赞同的话,他就不会和病人达成理解,而这在实践意义上来说,是不正确的——之所以不正确是应为这种做法提前出现,从而严重损害了病人的发展。也就是说,病人并不需要一个真理灌输给他——如果我们那么做了,我们仅仅达到他的头;他需要更多,才能成长到触碰这个真理,以此方式,我们才能达到他的心,而且这种作用进行得越深入,功用越有力。
315当医生片面的解释,仅仅是建立在要同意理论或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时,那么他说服病人或获得任何治疗成果的机会,就主要是依赖暗示了。任何人在此都不应自欺欺人。暗示本身不应受到鄙视,但是它有严重局限性,更不用说对病人的性格独立性有附带影响。从长期看来,我们的治疗要做好,是离不开性格独立性的。从业分析师也许应该绝对相信意识性认识的价值和意义,凭藉着意识性认识,本来是人格的无意识的部分被得以发现,经受意识的区别和评判。这是一个要求病人面对自己问题的过程,是一个消耗其意识判断和决定能量的过程。这一点也不亚于对其道德感的直接挑战,不亚于必须用整个人格回应的战斗号令。故而,在人格成熟这方面,分析性方法比暗示具有更高层级,暗示是一种暗中工作的魔术,而对人格没有道德要求。建立在暗示基础上的治疗方法是迷惑性权宜之计,它们与分析性治疗的原则不相容,而且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当然只有在医生意识到暗示可能性时,暗示才会被避免。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总是有足够的和超过足够所需的无意识暗示。
316希望排除无意识暗示的分析师,因此必须把每个梦的解释都当做是无效的,直到发现一个方案能赢得病人赞同之时。
317当处理那些梦——其费解性被证明是医生和病人双方都缺乏理解——时,对我来说遵守这条规则是至关重要的。医生也能应该把每一个这种梦都看做为新的东西,看作为和对他来说性质未知情况的资讯来源有关,关注这个情况他就和病人一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无需多说的是,他应该放弃他所有的理论假设,应该在对每一个单独个案时,都准备好建构其一种全新的梦理论。在这个领域中仍然有无穷机会去做开拓性工作。那种观点——认为梦仅仅是被压抑愿望的想像性满足——是完完全全的过时了。有些梦,的的确确,显然是代表愿望或恐惧,但是所有其他的东西呢?梦可以包含不可避免的真相,哲学性声明,幻觉,狂野的幻想、记忆、计画、期望、非理性的体验,甚至是心灵感应式图像,以及天晓得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有一件事情我们永远不应遗忘:我们的生命差不多有二分之一是在几乎是无意识状态中度过。梦是明确地无意识的表达。就像精神白天的一面我们称为意识一样,同样它也有黑夜的一面:无意识精神活动,我们把这理解为梦样幻想。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心灵不仅仅由愿望和恐惧组成,还有除此之外的许许多多东西,有高度可能的是,我们的梦精神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生命形式,和意识心灵的那些内容和生命样式对等,甚至更多,意识心灵的特性就是专注、限制和排外。
318既然如此,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应该缩减梦之意义,来符合某些狭隘教条。我们必须记住,有不少病人模仿医生技术或理论行话,甚至在他们梦中也如此,就像那句名言:Canis panem somniat, piscator pisces(译者注:拉丁语:狗梦面包,渔夫梦鱼)。这不是说渔夫梦到的鱼,就只是鱼,别无他意。没有什么语言是可以不被误用的。正如我们可以轻易想像得到的,这种误用经常会反作用于我们,甚至看起来无意识好像是有一种让医生吊死在自己理论圈套中的方法。因此在分析梦时,我尽可能地远离理论——当然,不是完全地,因为我们总是需要一些理论,使事物变得可理解。例如,正是在理论的基础上,我期望梦会有意义。我没法在每一个案例中,都证明事实便是如此,因为就是存在医生和病人不理解的梦。但是我必须做出这样的假设,为了鼓起处理梦的勇气。要是说梦给我们的意识知识增加了某些重要的东西,而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梦是因为没有被正确地解释,这种说法也是一种理论的话。但是我必须也做这种假设,为的是向我自己解释,为何我首先分析梦。然而,所有其他有关梦的结构和经验的假设也都仅仅是经验法则(德:handwerksregeln, 英:rules of thumb),必须接受持续的调整。在梦分析中我们必须永不忘记,即便一刻也不行,我们正走在变幻莫测之地,此处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如果不是如此自相矛盾的话,一个人几乎就会对梦解释者高呼:“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不要试图去理解。”
319当我们拿起一个费解之梦时,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要去理解和解释,而是要带着缜密关注,查明背景。这里我的意思不是指无限制的“自由联想”,从梦中的任何一个图像、每一个图像开始,而是小心的、有意识地阐明客观地围绕着特定意象的、相互联系的联想。很多病人首先必须接受这一点教育,因为他们就像具有无法克制地不加思索就理解和解释之欲望的医生一样,尤其是当他们被囫囵吞枣的阅读或之前误入歧途的分析错误引导时。他们开始根据理论进行联想,也就是说,他们力图解释和理解,而他们几乎总是陷入困境。就像医生一样,在错误地相信梦只是一个遮掩真实意义的外立面(facade)这一信念指导下,他们想要立刻走到梦的背后去。但是大部分房屋的所谓外立面,绝对不是一种伪装,或欺骗性歪曲。相反,它遵循建筑的计画,经常显露出内在的布置。“显”梦图像(The "manifest" dream-picture)就是梦本身,包含了梦的整个意义。当我在尿中发现了糖,它就是糖,而不是蛋白的假像( facade),弗洛伊德所说的梦假像(dream-facade,译者注,也有译“梦伪装”), 是指梦的费解性,而这实际上仅仅是我们自身缺乏理解的一种投射。我们说梦有一种虚假的外表,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看透它。更好的说法是,我们正在处理的是像一个文本的东西,它是不可理解的,这不是因为有一个假像文本。文本没有假像,而只是因为我们没法读它。我们没有必要走到这样一个文本后面去,而是必须首先学会读它。
320正如我已经提出的,学会读梦的最好方法,就是查明背景。自由联想会让我一无所获,和它对我破译赫梯人碑文提供的帮助相差无几。(译者注:Hittite,赫梯人,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建立过帝国,约西元前1700—约前1200年处于繁荣时期,赫梯语,经证明是最古老的印欧语系语言,用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书写,在20世纪初获解密。)自由联想当然可以帮助我揭露我自身的情结,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不需要什么梦,我可以用一篇公告或报纸上的一句话就行了。自由联想可以把我所有的情结带出来,但是几乎不能带出梦的意义。要理解梦的意义,我必须尽可能地贴近梦的意象。当某人梦到一张“松木桌”,就此联想到他那恰好不是松木做的写字桌是不够的。假定梦者就此没有想到更多,这种阻碍有客观的意义,因为它提示一块特别的黑暗笼罩着梦意象的最邻近领域,而这是可疑的。我们会期望他对于松木桌子有成堆的联想,而事实是,没有出现什么东西其本身是明显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断地回归到意象,并且我通常会不断对我的病人说,“假设我对‘松木桌’这个词的意义,一点概念也没有。描述一下这个物体,并告诉我它的历史,这样,让我对理解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不会产生偏差。”
321以这种方式,我们设法查明几乎是梦意象的整个背景。在我们对梦的所有意象做了这个工作后,我们才准备好瞭解释的探险。
322每个解释都是一种假设,一种阅读未知文本的尝试。费解的梦,如果孤立地来看,几乎不能有任何确定解释。因此我对单个梦的解释,几乎不予重视。只有在对一系列梦的解释中,才可能达到相对的确定程度,在系列梦中,后面的梦可以纠正我们在处理那些发生在前的梦时犯下的错误。而且,在系列梦中,基本理念和主题可以被更好地认识出来,所以我会力劝我的病人们详细记录他们的梦以及相应解释。我也会向他们显示,如何以上述的方式对他们的梦进行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梦及其背景以书面形式带到谘询中来。在较后的阶段,我让他们也对梦进行解释工作。以这种方式,病人学会了如何正确地处理无意识,不用医生的帮助。
323要是梦仅是有关病因学重要性因素的资讯来源,别无他物,那么我们可以稳当地把释梦的整个工作留给医生。再说一遍,如果梦的唯一用处就是提供给医生一堆有用的线索和心理学提示,那么我自己的程式就完全是多此一举。但是正如我举出的例子所证明的,既然梦包含着某些东西,多过于对医生的执业帮助的东西,那么梦分析就值得引起非常特别的注意。有时候,真的,它是生死攸关之事。在此类的很多例子中,有一个是给人留下尤其深刻印象的。这关系到我的一位同事,一位年纪比我大一些的男子,我过去不时见到他,他总是就我释梦这件事戏弄我。好,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他,他对我大叫:“怎么样啊?还在释梦吗?随便说一句,我又做了一个白痴梦。那也有什么意思吗?”这就是他所梦到的:“我在爬一座高山,越过陡峭的、盖满白雪的山坡。我越爬越高,天气非常好。我爬得越高,感觉越好。我想,‘要是我像这样永远爬就好了!’当我达到山顶,我是如此地快乐,如此兴高采烈,以至于我感觉到我可以飞升进入空中。然后我发现我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我飞升向上,进入空空的空气中,在十足的狂喜中醒了过来。”
324一阵讨论后,我说,“我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不能放弃登山,但是让我恳请你从现在其不要独自去。你要去的时候,带上两个向导,并以你的名誉承诺,绝对跟从他们。”“无可救药!”他回答,大笑,并挥别。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两个月后第一场打击降临了。他单独出去时,被一场雪崩埋住了,但是恰好被一队偶然经过的军事巡逻队挖了出来。三个月后,末日来临了。他继续和一个年轻一些的朋友去攀登,但是没有带向导。一个站在下方的向导看到,他在要下降到一块石头表面时,真的就踏出去到了空中。他落在他朋友的头上,这朋友正在稍下方等待,两人都摔倒遥远的谷底粉身碎骨。那真是乐极生悲!
325无论何种程度的怀疑和批评,都尚未能使我把梦看做是可忽略的偶发事件。它们经常会看起来非常无意义,但是这显然是我们缺乏理解力和机智,来阅读来自精神的夜间领域的谜样资讯。看到我们的精神至少有一半是在那个领域中度过的,看到意识作用于我们的夜间生活,就像无意识投影于我们白日生活一样多,似乎医学心理学更加需要义不容辞地通过系统研究梦,让自己的理解力变得敏锐。没有人质疑意识体验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质疑无意识事件的意义呢?它们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有时候是生活更真实的一部分,无论祸福,比起白天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更真实。
326既然梦提供的是隐藏的内心生活的资讯,而向病人揭示的那些人格成分,是在他白天行为中,仅仅表现为神经症症状的,那么顺理成章地,我们就不能仅仅从意识这一面去有效地治疗他,而是必须在无意识中促发改变,并通过无意识促发改变。就我们目前所知,这只有通过彻底的、有意识地对无意识内容的同化达到。
327同化(Assimilation)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意识和无意识的交互渗透,而不是——如通常所想和所做的——一种单方面由意识心灵进行的对无意识评价、解释和变形。关于无意识内容一般的价值和意义,非常错误的观点现在正流行。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从一种彻底负性的角度来呈现无意识,就像他们认为原始人比怪兽好不了多少一样。其有关部落老人的童话故事,以及其有关“幼稚-变态-犯罪的”无意识的说教,已经导致了人们把某些完全自然之物变成了危险的吃人魔鬼。就好像一切美好的、合理的、有价值的、美丽的东西都驻扎在意识心灵一样。难道世界大战之恐怖,丝毫没有让我们睁开眼睛,让我们仍然不能看到,意识心灵甚至比无意识的自然性更加邪恶,更加变态吗?
328最近指向我的指控是,我有关同化无意识的学说,会逐渐损害文明,把我们的最高价值移交给十足的原始性。这种观念不过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假定基础上:即无意识是头怪兽。这种观点起源于对自然和生命现实的恐惧。弗洛伊德创造了升华这个理念,把我们从想像中的无意识巨爪中拯救出来。但是真实之物,现实所存在之物,是不能被炼金术式地升华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明显被升华了,那么它从来就不是错误的解释所以为的那样。
329无意识不是一个恶魔样怪兽,而是一个自然实体,它就道德意义,审美趣味和知识判断而言,是完全中性的。只有在我们对它的意识态度是全然错误之时,它才会变得危险。随着我们压抑它的程度加深,它的危险性也就提高。但是随着病人开始同化以前无意识的内容的时刻到来,其危险性也就消失了。人格的解离,对精神的白日面与夜间面的焦虑地划分,随着渐进的同化而停止。我的批评者所恐惧的——意识心灵被无意识淹没——更有可能继发于无意识通过被压抑、被错误地解释和被贬低,而被排除于生活之外。
330关于无意识的自然本质的基本错误,大概是这样的:一般会假设,无意识的内容只有一个意义,而且会用一个无可变更的加号或减号来标示。依鄙人之浅见,这个观点太过幼稚。精神是一个自调节系统,就像躯体一样会维持其平衡性。任何太离谱的过程,立刻且无可避免地会引发补偿,而要是没有这些补偿过程,就既不会有正常的代谢,也不会有正常的精神。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可以把补偿当做是精神行为的基本法则。一边太少会造成另一边太多。同样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也是互补的。这一原则是在梦的解释中得到了最好证明的原则之一。当我们开始解释梦的时候,如此问总是有益的:这个梦是要补偿什么样的意识态度?
331补偿一般来说并不是仅仅一种虚幻的愿望满足,而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我们越是压抑它,它变得越真实。我们不会因为压抑自己的口渴,就能停止感觉到口渴感。同样的,梦的内容需要我们带着严肃的态度去看待它,把它看做一个事实,一个必须作为一个共同决定因素和意识态度进行配合的事实。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只会继续持有心灵的偏移的框架,而正是这种框架首先继发了无意识的补偿。然后就很难看到,我们如何能够对自己有明智的判断,或达到平衡的生活方式。
332如果出现有人想要用无意识内容替代意识内容这种情况,而这就是我的批评者们认为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可能性,那么这个人只是能够以压抑的方式成功,而这些内容接着会再次作为无意识补偿出现。无意识因此会彻底改变其面目。它现在变得胆怯而具有理性,跟其以前的风格截然相反。一般来说,人们不太相信无意识会如此行事,然而此种逆转频繁发生,构成了其固有的功能。这是为什么每个梦是一个资讯和控制的器官,以及为什么梦是我们建设人格的最有力助手的原因。
333无意识自身并不怀有任何爆发性材料,除非是自负的或怯弱的意识态度已经秘密地在那里储存了大量的爆发性之物。故而更有理由需要小心从事。
334从这一切看来,现在这一点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我何以在释梦时要制定一个试探性规则,问我自己:梦要补偿的意识态度是什么?通过这么做,我把梦尽可以地和意识情结联系。的确如此,我甚至会主张,没有意识情境的知识的话,梦永远也不能被带有任何确定性地解释。只有鉴于这种知识,才有可能做出无意识内容是带着加号还是减号的判断。梦不是一个彻底和日常生活切断的独立事件,缺乏其自身个性。如果梦对我们看起来是如此的话,这只是我们缺乏理解的结果,是一种主观错觉。实际上意识心灵和梦具有严格的因果关系,而且它们以最微妙方式互动。
335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表明,正确评估无意识内容是多么重要。一个青年男子带给我如下这个梦:“我父亲正驾驶着他的新车要离开家。他开车很笨,我对他那么愚蠢很恼火。他一会这边,一会那边走,一会向前,一会向后,把车开到危险的位置里。最后他撞到了墙,车毁坏得很严重。我怒气冲天,对他咆哮,告诉他应该检点自己行为。我父亲只是大笑,然后我看到他原来是醉得半死。”事实上这个梦毫无根据。梦者确信他父亲永远也不会如此行事,即便是喝醉了也不会。父亲作为驾驶员自己是非常小心的,在饮酒方面非常节制,尤其是他自己必须驾驶时。糟糕的驾驶,即便是对车有轻微损伤,也会让他大发雷霆。他和父亲的关系是正面的。他崇拜父亲,因为父亲是非同寻常的成功人物。我们可以说,不需要任何伟大的解释技艺,梦呈现了一副父亲让人不快的图像。那么对于儿子而言,我们应该从中得出什么意义呢?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仅仅是表面上好,而这组成了过度补偿的阻抗吗?如果是这样的的话,我们就必须给梦的内容一个正性符号,我们应该告诉年轻人:“这就是你和你父亲的真正关系。”但是既然我在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中找不到任何神经症性矛盾性,我没有任何依据用这么一个毁灭性宣言去扰乱年轻人的感情。这样做的话会是糟糕的治疗错误。
336但是,如果他和其父关系实际上是好的话,为什么梦会制造出这种出人意料的故事来贬损父亲呢?在梦者无意识中,必然有某种制造此种梦的倾向。也就是他究竟是不是有抵抗心理,这抵抗也许是由嫉妒或另外某种自卑动机所滋养?在我们径直开始让其良心背负重担前——这对敏感的年轻人来说,总是个相当危险的过程——我们最好不要探询他为什么做了这个梦,而是找到这个梦的目的是什么。在此个案的回答会是,他的无意识显然试图杀杀父亲的威风。如果我们把这看做是一种补偿,我们就不得不做出的结论是:他和父亲的关系不仅是好,而是实际上太好了。实际上,他配得上法国所称的“fils a papa”(法:爸爸的乖宝宝)称号。其父亲仍很大程度上是他生存保障者,而梦者仍然过着我称之为“暂时的生活”(provisional life)。他特有的危险是,他不能看待自身要依赖父亲之现实,从而无意识采取一种人为亵渎,为的是降低父亲,抬高儿子。“这样不道德,”我们可能会忍不住说。不具理解力的父亲可能会把此当做是冒犯,但是这正是合适的(zweckmäßige)补偿,因为它让儿子能够反对他的父亲,这是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唯一方法。
337刚才所列出的解释显然是正确解释,因为它直击要害。它赢得了梦者自发的赞同,而没有损害到任何真实的价值观念,无论是父亲的还是儿子的。但是只有当父子关系的整个意识现象被仔细研究后,这种解释才成为可能。对意识情结没有瞭解,则会对梦的真正意义存有疑惑。
338为了要让梦-内容得到同化,首当其冲的就是意识人格的真实价值观念不应该受到损害,更不要说被摧毁了,要不然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可供同化的了。认识无意识不是一场布尔什维克实验,把底层翻到顶层,这样做只会重建恰恰是它当初意图更正的情境。我们必须呵护意识人格的价值,让它保持完整,因为只有当无意识和整合性意识合作时,其补偿才是有效的。同化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既有此,又有彼”。
339正如对梦的解释要求对意识现状的确切瞭解一样,对待梦的象征同样也需要我们考虑到梦者的哲学、宗教和道德信仰。在实践中较为明智的是,不要仅从语意上看待梦象征,也就是,不要把梦象征当做是一种固定特性的征兆或症状,而是把它们当做真正的象征,也就是,当做是仍未被有意识地认识到或尚未有概念形式的内容之表达,除此之外,它们必须被认为是和梦者的当前意识状态有关的。我之所以建议这个程式,因为理论上相应固定的象征是的确存在的,而其意义绝对不要被当做一个概念,指向作为任何已知和已有形式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相对固定的象征,则没有可能来决定无意识的结构,因为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以任何方式来把握或描述。
340我会对这些相对固定的象征,赋予一种貌似不明确的内容,这也许看上去有些奇怪。然而如果它们的内容不是不明确的,它们就根本不是象征了,而是征兆或症状。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学派是如何运用硬性严格的性象征——这种硬性严格的情况我会称之为“征兆”(sigh)——并且赋予它们一个明确确定的内容,也就是性欲。不幸的是,弗洛伊德的性的理念极其多变,十分模糊,以至于它可以用来包括几乎任何东西。“性欲”这个词听起来非常熟悉,但是其所指称的仅仅是一个不确定的变数X,其范围从腺体的生理活动这一端,到另一端是灵魂的无上成就。我不会屈从于建立在错觉基础上教条式信仰,这种错觉是仅仅只因为我们使用了熟悉的词语,并以为我们瞭解了某事,相反,我更愿意把象征看作是未知参量,它是难以认识的,而且,归根结底,永远都是不十分确定的。就以所谓的阳具象征来说,它们被假设代表着男子雄风的阴茎,除此之外并无他意。从心理学上来讲,阴茎(membrum)它自己——正如Kranefeldt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指出的——是某些东西的象征标志(emblem),其广泛的内容根本不容易确定下来。【注:指Kranefeldt所着,Komplex und Mythos ,102】 但原始人就像古人一样,极为自由地使用阳具象征,做梦都不会把作为仪式象征的阳具和阴茎混淆起来。阳具总是意味着创造性神力(mana), 疗愈和繁殖的力量,用李曼(Lehmann)的说法,就是“超常的欲力”,其在神话中和在梦中的对等物是公牛,驴子,石榴,约力(yoni,译者注:印度教中,作为神授生殖能力象征,通常以一圆形石头代表,另一义为女性外阴。), 公羊,闪电,跳舞,犁沟里的魔力性交(cohabitation ,Beischlaf, 译者注:感应巫术一种,指有些民族会在春耕时在犁沟中性交,以期望生殖力带来好收成),月经流血,这里提到的还只是成百上千各种类比的一小部分。潜伏在所有类比之下的,以及潜伏在性欲本身之下的,是一种原型意象,其特性是很难定义的,但是其最接近的心理对等物也许是原始的神力-象征。
341所有这些象征是相对固定的,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有先验的确定性,可以让我们说,在实践中象征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解释。
342 实践需要也许要求某种全然不同之物。当然,如果我们必须给梦一个彻底科学的解释,以符合某一理论,我们就会不得不把每一个此类象征都归结到原型上。但是在实践中,那可能会是完全的错误,因为病人在当时的心理状态,也许需要的是其他东西,而绝非离题进入梦理论中。故而会建议首当其冲的是,要考虑象征的意义和意识情境之关系,换句话说,对待象征要把它看做是不固定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放弃所有先入之见,无论它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多么地有知识,并试图发现事物对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显然朝着理论解释的方向走得太远,实际上我们也许在开始时会被陷住。但是如果执业者太按照固定象征操作,就会陷入仅仅是例行公事和恶劣的教条主义,从而让其病人失望。不幸的是,我必须克制自己不说明这一点,因为那样就会有太多细节,这里的篇幅不允许。而且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发表了足够的材料,支持我的陈述。
343经常发生的是,在治疗刚一开始的时候,梦就会以广阔的视角,向医生揭露整个无意识的方案,但是由于实践的理由,要想让病人此刻就明白梦的较深刻意义,会是不太可能。在这个方面,同样,我们也受到实践考量之限制。这种领悟的得出,也许是由于医生对于相对固定象征的知识。它对于诊断和预后有最大的价值。我有次给一个17岁的女孩谘询。一个专家已经推测,她可能处于渐进性肌萎缩的初级阶段,然而另外一位认为这是一个癔症个案。因为第二种意见,我被请去了。临床表现让我怀疑这是器质性疾病,但是也有癔症之征兆。我要求她说梦。病人立刻回答:“是的,我有些可怕的梦。就在最近我梦到我在夜里回家。每样东西都像死一样安静。进入客厅的门半开着,我看到我母亲吊在枝形吊灯上,在冷风中来回摇摆,风是通过开着的窗户吹进来的。还有一次,我梦到夜里房子里爆发出可怕的噪音。我起床后,发现一匹受惊的马正在房间中左右奔走。最终它发现了到大厅的梦,并跳出了大厅的窗户,从四楼一直落到下面的街道上。当我看到它躺在那里,面目全非,我吓坏了。”
344这些梦的恐怖特性就足以让人却步。尽管如此,其他人时不时也会做焦虑梦。故而我们必须更加贴近到两个主要象征“母亲”和“马”的意义中。它们肯定是对等物,因为它们都做同样的事情:它们实施自杀。“母亲”是一个原型,指向起源之地,指向自然,指向被动创造者,因此也就指向材料和物质,指向实体性,子宫,生长营养功能。它也意味着无意识,我们的自然和本能生命,生理领域,我们居住于其中或被包容其中的身体,因为“母亲”也是母体,是空洞形状,是承载和营养的血管,从而它心理上代表着意识的基础。成为在内者或者被某物包容,也暗示着黑暗,某种夜间、恐怖的东西,把人包围起来。这些隐喻给了母亲这个意念很多神话学和词源学的变化,它们同样代表着中国哲学中“阴”这个意念的重要部分。这不是一个17岁的女孩通过个人生活获得的,它是集体的遗产,存活并被记录于语言中,随着精神的结构而遗传下来,从而会可以在所有时代所有人中发现。
345“母亲”这个词,听起来如此熟悉,显然是指向人所共知的、个体的“母亲”,指向“我的母亲”。但是母亲-象征指向更黑暗的背景,它规避了概念形式,只能被模糊地领会为身体的隐藏的、自然联接的生命。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太狭隘了,排除了太多重要的附带意义。潜在的、原始性的精神现实,是如此复杂不可思议,以至于它只能通过最大限度的直觉可以得以把握,但是也仍然是非常模糊含混的。这是为什么需要象征的原因。
346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发现运用到梦上,其解释将是:无意识生命正在摧毁自身。这是梦给梦者的意识心灵的资讯,给任何有耳朵能听见的人的资讯。
347“马”是一个在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广泛流传的原型。作为动物它代表着非人类的精神,次人类,动物面,无意识。这就是为何民间传说中马有时候能够看见幻象,听到声音,并说话。作为一种承载的野兽,他和母亲原型联系紧密。如瓦尔基里背着死去的勇士到瓦尔哈拉,如特洛伊马,(译者注:瓦尔基里Valkyries 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战神奥丁的助手,负责将自己选中的阵亡勇士引入瓦尔哈拉Valhalla殿堂),作为一种比人类低级的动物,马代表着身体的较低部分,和从那里升起的动物冲动。马是动力性和运载性能量:它把人带走,就像一股本能一样。它服从于惊恐,就像所有的缺乏较高等意识的本能性生物一样。而且,它必然与妖术及神秘咒语有关,尤其是和预示死亡的黑夜之马(black night-horses)有关。
348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那匹“马”是“母亲”的对等物,只是意义稍有变迁。母亲代表着生命本身的起源,而马仅仅代表着身体的动物性生命。如果我们把这个意义运用到我们这个梦的文本,其解释就是:动物性生命正在摧毁它自身。
349这两个梦做出了几乎是相同的陈述,但是,就通常情况而言,第二个梦是更加明确的。请注意梦中特有的微妙之处:并没有提到个体的死亡。众所周知人常常会梦到自身的死亡,但是这并不是稀奇之事。当真正涉及到死亡问题的时候,梦会说另一种语言。
350两个梦都指向严重的器质性疾病,有致死的结果。这个预后不久得到了证实。
351至于说到相对固定的象征,这个例子给出了一个它们普遍本质的相当不错的说明。存在很多这样的象征,所有都由于意义的微妙变迁,而具有个体性标志。只有通过神话、民间传说、宗教和哲学的比较,我们能够科学地评估它们的本质。精神的进化性层次在梦中比在意识心灵中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辨别。在梦中,精神通过意象说话,并让本能得以表达,而本能往往是起源于最原始的自然本性的层面。因此,通过对无意识内容的同化,意识的短暂生命能够再次被带入和自然法则的和谐共存中,意识是很容易背离自然法则的,同时病人也能被带回到他自身存在的自然法则中。
352我不能,在如此短的篇幅中,涉及所有事情,而只能涉及和主题相关的要素,我不能在你们眼前,垒砖叠瓦地把整个大厦堆聚起来,此大厦之竖立来自于每次分析的无意识材料,最终达成了整个人格的重建。连续性同化作用的方式远远超越了和医生特定相关的治疗结果。它最终导致的远期目标,也许一直都是生命的第一冲动——整个人性存在的完整实现,也就是,自性化。我们医生也许正是对此自然本性黑暗过程的第一批意识性观察者。通常我们只看到这个发展过程的病理性阶段,而一旦病人被治疗好,他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然而,只有在治疗之后,我们才会真正处于研究正常过程的位置上,而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年、数十年。要是我们对无意识发展走向的目标有一点点知识,要是医生们的心理学领悟不仅仅是单独从病理阶段获得,那么我们应该会对经由梦传递的这些过程,有更少一些的困惑理念,对象征的指向有更明确认识。以我之见,每位医生都应该理解,心理治疗的每个程式,尤其是分析性程式,会分解为一个有目标的、持续的发展过程,一会儿在这一点,一会儿在那一点,随之就会凸显出一些独立的阶段,它们看起来跟随着彼此矛盾的进程。每一个个体的分析它自身只是展示出更深刻过程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因此,比较案例的历史,其结果只会是得到绝望的困惑。也正是因此,我更乐于限制我自己只讨论这个主题的基础,并限于讨论实践的考量,因为只有在和日常事实的最密切接触中,我们才能获得类似于“满意地理解”这一东西。
-
 通过本次学习,获益匪浅,梦的工作方法和步骤以及经验丰富(0) 回复 (0)
通过本次学习,获益匪浅,梦的工作方法和步骤以及经验丰富(0) 回复 (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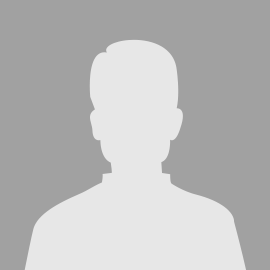 很好(0) 回复 (0)
很好(0) 回复 (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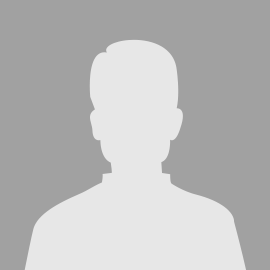 值得反复读几遍!(1) 回复 (0)
值得反复读几遍!(1) 回复 (0) -
 签到(0) 回复 (0)
签到(0) 回复 (0) -
 理解满意(0) 回复 (0)
理解满意(0) 回复 (0) -
 学习了受益匪浅(0) 回复 (0)
学习了受益匪浅(0) 回复 (0) -
 学习了(0) 回复 (0)
学习了(0) 回复 (0) -
 理解与否,梦在那里(0) 回复 (0)
理解与否,梦在那里(0) 回复 (0) -
 梦太宝贵、太神奇、太复杂!(0) 回复 (0)
梦太宝贵、太神奇、太复杂!(0) 回复 (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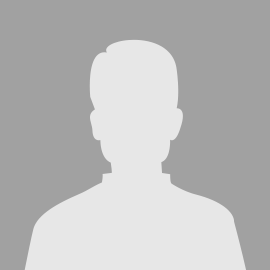 学习了,收获很多,还需要再细细读几遍(0) 回复 (0)
学习了,收获很多,还需要再细细读几遍(0) 回复 (0)
